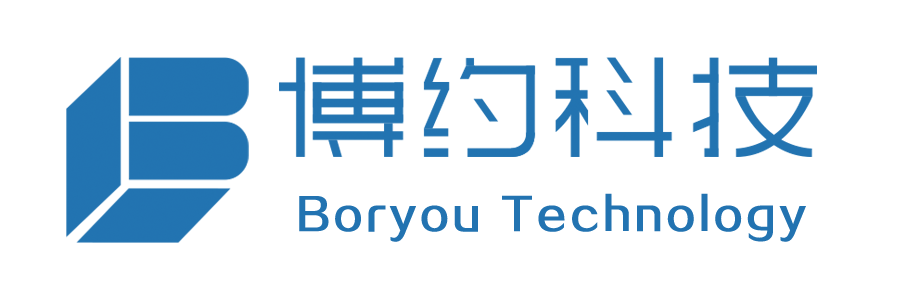關于近期幾起網絡舉報熱點事件的一個總結
近期發生了多起網絡熱點事件,比如人大女博士生網絡舉報自己導師猥褻事件、江西縣委書記毛奇被舉報事件、中信建投實習生網絡炫富事件,以及陸續發生的多起高校女生舉報老師事件。
類似多起事件,包含著一個關鍵詞,那就是“網絡舉報”。
如不是網絡舉報,誰會知道一個學富五車的大學教授,精神世界竟如此令人難以直視呢?教授并不掌握公權力,因此王某某這種行為不是人所共知的公權力腐敗,而是社會腐敗。其特征在于,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某種權力,比如學術權力、把關權力、道德權力,甚至掌握了某種優勢資源,就會用來裹挾弱者,謀取私利,直到進行身體的性剝削、心理剝削。今天需要單獨拎出來“社會腐敗”進行社會批評。
如果不是網絡舉報,誰會相信縣委書記權力真的如此巨大并且不受約束呢?正如一些網民說的那樣,這位書記竟然在女子打算舉報之前,先下手為強,迅速對其進行留置。相關部門成為打手和工具。如此強權,讓人不寒而栗。什么是縣域的強權?那就是縣委書記表面上說能夠為民服務,也能夠利用權力為百姓創造一些財富,但是也能一夜之間翻臉,把百姓包括下屬的權利全部剝奪,監督如同虛設。
近期密集的網絡舉報,讓很多人身心不舒服。認為打亂了社會秩序,網絡出現了狂歡,更可能影響社會的穩定,還可能鼓動出現更多的網絡舉報,讓一些人生活于惶恐不安的陰影之下,也導致單位負責人時時擔心事態脫離于掌控之外,“可千萬不要出什么亂子!”
問題在于,這些網絡舉報曝光出來的,都是什么性質的東西?是真善美,還是假丑惡?如果曝光的是假丑惡,正如陽光穿透了霧霾,這又有什么問題呢?難道要維護假丑惡,給它找庇護所嗎?那不成了假丑惡的保護傘嗎?或者說,反對曝光的人,是站在假丑惡一邊的?如果有助于曝光假丑惡,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從而推動社會進步,讓群眾感受到安全感的,讓社會變得更為美好的行為,都會獲得百姓的支持,從而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這種行為,本質上是一種群眾監督行為,是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組成部分。
其實從中國網絡輿情的歷史看,輿情的爆發,常常都是網絡舉報的結果。一部網絡輿情史,更多是一部網絡舉報史和爆料史。因此,我們應該見怪不怪了,并且已經將這種舉報和爆料,納入了制度化建設的渠道之中。
實質上,上面擔心網絡舉報的人們,應該這樣追問:為什么網絡輿情出現了數十年,今天的網絡舉報依然層出不窮?
就以高校網絡舉報來說,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呼吁,該校要以此案為契機,建設起一套便利的、具有公信力和效率的舉報渠道,不光保護弱者,也對掌握權力的那些蠢蠢欲動者形成威懾和嚇阻。實際上,多年來類似事件出現之后,已經引起專家學者、法律工作者和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推動了高校進行了類似渠道的建設,一些政策制度已經相當規范和嚴密。
比如高校有舉報信箱、師生糾紛調解處理機制、教師代表大會、師生關系聯席會議、校長信箱、師德建設委員會等等。從邏輯和理論上,這一條制度建設已經相當嚴密而工整,任何有敢于作奸犯科者,一旦觸犯紅線,等待他們的必然是身敗名裂的下場。但是實際上,這套制度長期和蠢蠢欲動者乃至作奸犯科者相安無事,就如同很多電網一樣,實際從不通電,熟知規則者視之如無物。顯然,這一套并沒有發揮作用。如果沒有發揮作用,那它存在的意義就是敷衍,就是形式主義。
從現實看,精致的形式主義正成為不少地方應對網絡輿情的一個法寶。中國網路輿情爆發幾十年里,倒逼了地方政府從漠視輿情,到重視輿情,到今天的開始行動起來,呼應輿情,和輿情進行互動。這很顯然是個巨大的進步。但是不能不說,進步了卻沒有進步到位。我們常常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員發展出了一套精致的形式主義和輿情進行互動,這表現為:能迅速發現輿情并進行通報,但是接下來的調查就充滿了心機,高舉輕放,避重就輕,字里行間充滿了顧慮重重和地方保護主義,但是百姓關心的核心問題刻意繞過,非重點卻濃墨重彩,細節描寫堪稱教科書。以太極拳和網絡輿情和群眾呼聲進行互動,導致了網民愿望落空,后者遲遲得不到滿足,從而這套形式主義也就慢慢暴露出了真面目。
很多形式主義如同在防彈衣,或者隱藏目標的偽裝系統,只是為了降低網絡輿情的傷害程度,或者讓網絡輿情找不到目標,找不到隱藏的問題的根子,從而應對了輿情。這實質是應付輿情,敷衍了事。
群眾并非傻瓜。網絡已經以網絡輿論的方式,或者推出意見領袖的路徑,生產出了一套網絡智慧和群體智慧的萃取方式。無數網民的想法如同富集的咖啡豆,這套機制能夠萃取出咖啡豆的精華。網絡將人民群眾中最有智慧、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或者最能代表當下社會心理的觀點,以及提出這種觀點的人,呈現在網絡最為顯眼的地方,成為網絡輿論,推舉為意見領袖。比如熱搜、高贊的留言自動提升排位等機制,也是這樣的形式。通過這種網絡賦權的方式,網民和群眾常常毫不留情地將問題點破,讓試圖敷衍了事的形式主義無處藏身。
但是精致的形式主義采取了敷衍的態度應對問題,假裝看不到問題所在,導致了地方政府、大型機構和網民之間出現真正的疏離,以及更多的不信任感。也導致了一些陰謀論漸漸成形,流傳于民間。再加上今天的社交圈層傳播和算法推送機制,這種“陰謀論”強化了階層的群體心理,強調了彼此身份認同,從而可能導致更大的社會撕裂。
很多地方的領導干部最大愿望是任職期間不要出事,慣于以擺平作為水平,為此形式主義愈演愈烈,至于由此留下的爛攤子和公信力問題,并不在他們考慮范圍之內。地方被他們視為升官升空的“發射場”,只要順利升空,哪管發射場變成一片廢墟。但是相關主管部門和上級部門,卻不能對此視而不見。
再以縣委書記掌握的的重權來說,多年來已經出現了一些監督機制,以約束其過大的權力,很多地方確實見到實效,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能找到很多方法逃避監督,依然大權在握,放任無忌。當然,網絡輿情是最大最快的監督性“解藥”,但是經濟社會發展落后的地方,網絡輿情爆發也較慢較少,導致了監督藥方遲遲未到。在縣域范圍之內,權力處于主導性的地位,縣委書記處于權力結構的金字塔的塔尖,因此進行權力的監督,防止濫用和私用,是制度建設和社會建設的重中之重。
所以說,網絡舉報在今天依然頻頻發生,并不是說過去數十年的網絡輿情洗禮沒有推動制度的建設,相反,不少制度框架是有了,但是制度被閑置,演變成了形式主義。輿情推動的社會進步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即便是我們批評的形式主義,也是一種進步,起碼在形式上具備了一些保障民眾知情權的渠道,和可以使用的維權工具,不過是在現實中很多已經有的制度不能啟動。正如一把槍,沒有扳機,或者有扳機,卻無觸動機制。這也相當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正是人們不信任這樣的形式主義制度,只能采取網絡舉報的方式。這也是今天網絡舉報依然頻發的一個根源。
一旦網絡輿情爆發,學校就會迅速行動起來,然后快刀斬亂麻,事件當事人會被當做垃圾一樣,被打包甩出校園。這樣從重從快的做法,當然符合網民“快意恩仇”的道德訴求,但是常常會對制度帶來傷害。已經有學者指出,類似這種沒有調查、直接以行政權代替法律和學術調查的方法,不光沒有維護當事人的應該有的權益,也將制度視為無物。長此以往,反倒強化了行政權力的權威,而制度建設和各種委員會處于邊緣化狀態。
總之,如果現實社會中已經有的一套規章制度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繼續讓它們成為擺設和形式主義的道具,那么網絡舉報依然不會降溫,會繼續成為社會熱點爆發的導火索。
同時,有了制度,還需要取信于民,讓弱者相信通過制度舉報是有用的。就是說,增強弱者舉報的信心,打造制度的確定性。如果制度再好,但是弱者并不相信你,依然相信網絡舉報是最好的,那么制度建設依然是失敗的,如同屠龍之術,花架子而已。
社會發展到今天,網民和群眾對于自己的權益意識的認識是非常清晰的,該維護權益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拿起武器,這個武器就是網絡舉報。網絡輿情一直以來就是弱者的武器。在現實中、在線下,弱者是難以對抗強者的,但是一旦上網爆料,全體網民都成為聲援者和強大后盾,強者立馬變為弱者。
所以,各地、各單位和相關負責人如果不能真正從問題意識入手,將解決問題當做執政的思路,那么無疑就是將更多問題推到網絡,推動網絡舉報和網絡爆料。而一旦輿情爆發,又轉過來會成為所在單位負責人的麻煩和問題。因為解決輿情問題也是一把手的責任。就是說,如果不能從源頭上推動制度建設,并將制度付諸實施,那么自己會成為最后的責任承擔者。舉報者搬起了石頭,最后也會砸到負責人的腳。
我們在前文也提到過,一些重大網絡輿情的通報,說服力漸漸降低,重建公信力和取信于民的努力,變得更為困難。這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今天一些貧富懸殊現象導致的沖突現象和網絡輿情,解釋陷入了困境。從網民角度看,有的富者帶有原罪;但是從改革發展等角度看,富者卻是發展的結果,具有時代的合理性。一種觀點、一個輿論難以包打天下,是今天的一個現實困境,但是這種困境,僅僅是相對于過去而言,觀點的多元,本來就是一個發展的結果和標志,因此是合理的。當然,網民的訴求和渴望水漲船高,也是一個因素。他們近年來更為痛恨腐敗和不公平現象,希望中央領導各地正本清源,滌蕩一切假丑惡現象。發展改革的求穩求全,和他們求快求重心理之間,出現了落差。打破這種僵局的關鍵,是讓人們看到決心和希望。人們對于未來的看法是樂觀還是悲觀,常常取決于想象力的好壞。
綜上所述,網絡輿情發展到今天,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形式具備了,現在需要的是踏實而具體的行動。就是在實踐中將很多已經出臺的政策法規切切實實地落到實處。比如高校那么多的制度政策,本就是防范師生關系的變異的,但是如今這么多的制度政策卻一無用處,大象一般身軀的嫌疑分子卻沒網住一個,反倒需要受害者拿高音喇叭進行曝光,這豈非笑話!
總結一下,當下網民的勇敢行動,以及輿情后果的嚴重性,已經倒逼我們需要進行真正的制度建設。已經建立起來的制度框架,更需要充實它。
從世界一些發達國家的實踐看,在進步主義為主的發展階段,每當出現一個重大的社會事件,都會緊隨其后出臺一個法律法規,或者強化了某種群體道德觀點,打上制度或者人性的“補丁”。而我們這里,每當一個重大網絡輿情爆發后,地方滿足于快刀斬亂麻處理個體,以情緒的安撫和輿情消退為最終結果和最大目標,制度結晶和社會共識常常乏善可陳。這導致了社會成本加大,也阻擋不了下一個輿情的再次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