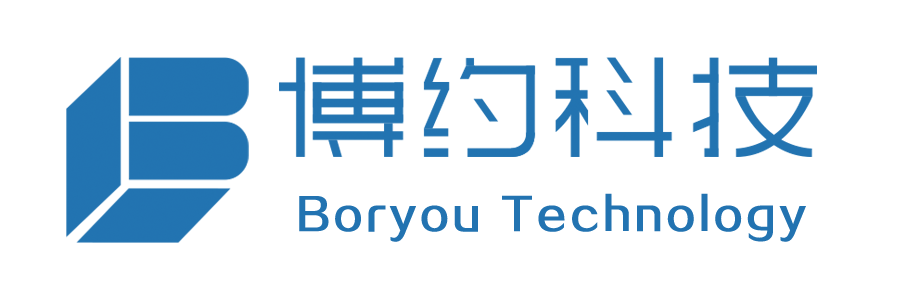從張雪峰“割韭菜”,看輿情多是低收入群體心理情緒現象
如果理解到,網絡輿情常常是網絡的群體心理和群體情緒現象,那么近年來的網絡輿情走勢,不斷出現爆點也就是正常的事情了。疫情期間自不必說,激烈的群體情緒導致熱點不斷;疫情之后,經濟不振又導致了社會心理低迷,反倒容易出現一些沖突事件和極端事件。經濟社會大形勢是大氣候,輿情不過是特地區域的天氣。
一、基層“輿情焦慮”是輿情回應的后果嗎?
輿情爆發頻仍,相關部門也加大了對于輿情的回應力度,一些通報也煞費苦心。網絡輿情對于基層社會的影響也在變大,“輿情焦慮”已經成為一種較為顯著的社會現象。比如,一些縣委書記和基層干部說,經常性的三分之一時間在處理輿情,還有一些時間在奔赴輿情現場的路上。下面輿情頻發,上面問責加大,中間的基層干部群體處于“夾板層”,再加應對無方,難免焦慮。內蒙古開魯縣的土地糾紛,央視對于安徽全椒縣的輿論監督等事件,可以視作是這種導致基層輿情焦慮的最新案例。
“輿情焦慮”并不必然是體制回應輿情帶來的后果,它應該看做是一種心理危機、本領危機,以及考核帶來的高壓現象,也是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客觀反映。隨著經濟發展的引擎重啟,焦慮現象會大大改善。
體制不能因為“輿情焦慮”而降低對于輿情的關注和回應力度。因為回應本身就是交流和溝通,具有安撫社會心理的作用,它提供了對于網民群體的情緒價值,對于社會穩定不可或缺。
同時,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從基層的“輿情焦慮”現象,看輿情熱點的走向和爆發規律》提出的觀點那樣,網絡輿情正在倒逼中國成為一個民主社會,公共輿論空間中的網民力量正在凸顯,各種權力、利益和觀點,都會放在網絡輿論空間中被政府部門、網民群體、意見領袖、各個階層乃至西方觀點、跨國資本等多方力量進行全方位觀察、考量和監視,意見市場逐步形成,多方激烈博弈,最后總會得出一個不那么壞的結論和結果。中國社會正是在這種喧鬧和沖突的互動中,走向進步和發展。因此,回應本身是和網民互動的過程,是個良性互動的過程,它本身具有民生和民主的意義。
但是大家也會發現,這一兩年來的網絡輿情中,水份和火氣成分更大,群體情緒的比重越來越凸顯。所謂“水份”,就是口水和唾沫增多,含金量下降;所謂“火氣”,就是網民更為敏感易怒,正如佩劍的武士時代,動輒拔刀相向,對峙嚴重。但是它們依然是網絡輿情和網絡輿論,依然值得敬畏。
二、多數輿情不過是低收入群體的心理現象
我考察了最近一兩年來的網絡輿情,有一個較為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大多數的網絡輿情,都是中低收入群體的群體心理現象,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群體心理、群體情緒現象。
如果不能用社會階層和網絡階層的觀點來考察中國的很多輿情現象,那么很多方面的認識會顯得膚淺。因為階層的出現,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階層集合了各自的利益、文化和觀點,具有鮮明的邊際感和階層力量。這使得不同階層,看待同一件事情,觀點也常常不同,或者有所差異。階層概念的使用,相比那些以年齡、城鄉居民身份、性別等來進行群體的劃分,顯得更為綜合,更有解釋力。
在網民構成中,中低收入群體的聲音歷來是響亮而激烈的。因為中國的網絡輿情本來就是一個低收入的弱勢群體的網絡抗爭的現象,它是一部中國社會發展史的重要構成內容。我的觀點是,中國中低收入群體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在改革開放幾十年后,借助新媒體和社交軟件在中國社會實現了第二次崛起。他們占據了中國各大互聯網平臺的每個角落,再加上算法推送的信息紐帶,以及社交軟件微信的圈層化的情感凝聚力量,他們從五湖四海,實現了網絡上的會師。
進而在各種大事件的輿論博弈中實現了利益和觀點的確認,進行了群體身份的認同,并在其他階層給出的“民粹思潮”的標簽下,以及“弱者即正義”的價值觀的統領下,他們成為了一個時而松散、時而嘯聚的網絡共同體。一個可能重新影響中國歷史發展走向和政策導向的網絡力量,正在出現,并且正在顯示力量。
但是他們在一些網絡熱點事件的觀點是矛盾的,一前一后的看法和情緒,常常是矛盾的。比如,他們天生同情弱者,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又普遍看不起弱者。人們慣于從看不起比自己更弱者的行為中,來尋找生活的動力和合理性。他們對于從底層拼搏而沖殺出來的網絡名人抱有好感,也因此捧紅了無數的網紅和網絡達人,但是一旦后者暴富了、露富了,或者炫富了,群體的情感傾向就改變了,不再追捧他們,甚至開始反感他們。但是那些一夜暴富的網紅,追求價值感和存在感的方式之一,就是時不時地炫耀一下成功,或者總是會言談舉止中間露出一點有錢人的蛛絲馬跡。如果人生不能衣錦還鄉,或者不能露富,這成功的價值何在?但是這擊中了低收入群體強烈的自尊,他們視之為背叛。
低收入群體還需要在中高收入群體中尋找自己群體的代言人,這會提高他們的社會價值感,獲得群體的信仰力量。比如他們曾經選定的代言人有司馬南、刀郎、董宇輝等人,他們也有比較信賴的人,如專門講解高考相關事宜的張雪峰等。
如果用上述階層的分析方法,以及用低收入群體的特點來看待一些網絡輿情熱點,以及其中的熱點人物,比如張雪峰、選調女生等,就能獲得如下的一些看法。
三、圍繞張雪峰的輿情,都是低收入群體的情感變化晴雨表
這兩天比較大的熱點,是隨著2024年高考臨近,網紅張雪峰再次陷入是非爭議。
這源于一直通過直播和網絡信息流,和中低收入群體進行陪伴和對話的張雪峰,突然割韭菜了,而且暴富了。據網絡信息,張雪峰提供的高考志愿填報課程,單價接近2萬元,依然被搶購一空,據統計很短時間內公司進賬2億多。這一下子讓很多家長感到很氣憤,認為張雪峰在割韭菜。
我在前文說過,張雪峰是窮人的福音。因為中高收入群體,他們有更多更好的渠道去了解有關高考和志愿的信息,他們的價值含金量更高,很多人已經不再關注國內高考了,或者有更好的升級路線圖。他們雖然有的也關注張雪峰,但是很顯然這只是他們的信息渠道之一,僅僅具有參考的價值。但是窮人和低收入群體不一樣,張雪峰是他們唯一的信息窗口,希望來源。
高考和文憑,進城和當官,是低收入群體所能想到的“鯉魚跳龍門”的不二法門,這實際也是中國社會階層垂直流動的最主要通道。但低收入群體在孩子求學和升學的過程中,最大的困境是自己無力為孩子的前程提供什么有價值的建議。這個階層出身的孩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考取大學,人生規范反倒一片空白,至于城市和專業如此重要之事,從未有所考慮。那些身處底層,依然固執己見、對孩子指手畫腳的家長,不過是試圖將孩子拉回自己身邊,向自己的人生看齊。為了給孩子更好的建議,成為家庭階層翻身的唯一希望,他們會向那些有學識的人們專門求教,但是他們周圍缺少這樣的資源。網絡紅利之一,就是為這個群體帶來了好消息,張雪峰在各個場合出現了,以他的伶牙俐齒和不時的吐槽利益既得者,以及在他們看來具有高度含金量的知識分享,獲得了他們的高度認同。再加上算法“一旦點擊,經常推送”的特點,這使得張雪峰牢牢占據了低收入群體的精神領域,成為他們的認知錨,成為他們的救星和福音。
但是“流量的盡頭是直播”“直播的盡頭是割韭菜”,張雪峰也是需要變現商業價值的,這么多年的辛苦直播,已經有了這么多的粉絲,割韭菜或許就是水到渠成。但是收割需要一個理由,要有個說法,所以張雪峰說:“不要期待在直播間用一個免費的連麥,去完成一個正常收費在一萬塊錢左右的一對一升學規劃。”顯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有也是不道德的,這就獲得了一個割韭菜的合理合法性。
但是問題在于,張雪峰的粉絲主體是低收入群體,他們中少數人會為了這個高價的項目,咬咬牙而買單,但是張雪峰需要承受為此產生的道德風險和輿情風險。
因為低收入群體本來是把你當做救星和信仰的,突然你有一天割韭菜了,這會引起他們的不滿。而且,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讓他們感受到了相對的剝奪,他們會認為,能買得起的都是有錢人,而他們自己作為弱者,無力付費,這就會引發他們內心的不滿,群體倒戈或者群體憤怒,就有了可能性。起碼他的聲譽,可能很難是眾口一詞地稱譽了。
所以說,圍繞張雪峰的一些網絡是非,不過是低收入群體的心理和情緒的變化晴雨表。
四、武大女選調生冒犯了全體低收入網民
最近,一位自稱來自985高校的女生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她因為對被分配至嘉峪關工作的不滿和嫌棄的言論在網上瘋傳,最終導致她黯然離職。
作為這位學生的母校,武漢大學也不得不站出來回應網民。因為如果不回應,網民就會加大火力。中國網民養成了這樣的思維,誰的孩子誰抱走。孩子不懂事,就找父母;員工惹了事,就找單位,一旦發現是國企央企,那就搞大了,乃至可能人肉他們的負責人。因為國企央企和大機構是輿情的常客,是不公平的淵藪,存在一個“破窗效應”。所以在今天,輿情管理是一把手工程,說不好某個一線的員工的惹的禍,將來就會成為領導要背的鍋。
但是我們需要回過頭來復盤一下,這個武大選調生的行為,為何在網絡引起了這么大的反響,得罪了這么多的網民?
我們需要理解,即便是一個農家的孩子,一旦考上了985,上了985的研究生,那就是鯉魚跳龍門成功,翻身做了主人,在中低收入群體的眼里,那就不一樣了,成了社會的“上等人”。今天的中高收入群體已經被低收入群體視為階層的對手,即便前者很多由底層脫胎而來,但是也不再是自己人。他們看985學生的眼光和心理,就悄然有了變化。看不起你窮,但是也看不得你“變闊”,這或許也是人性,而社會基層是基本人性的大本營,沒有受到現代文明的污染,快意恩仇,道德感強,保持了原生態,也經常爆發人性的流量。
所以當四川大學的張某,作為一個985的研究生,在網絡吐槽乃至網暴一個忠厚老實的打工者的時候,為何引發那么大的網絡輿情?就在于她再次演繹了網絡輿情中強弱對比鮮明的攻守故事,激起了無數網民的憤怒。在他們眼里,一個985的白富美的女研究生,攻擊一個低收入者,就犯下了一個道德罪愆,根據“弱者即正義”的價值觀,他們必然群起而攻之,使得張某成為網絡公敵。
再看武大選調生,履歷光鮮,一路985,但是成為選調生,委派到她自認為較為偏遠的嘉峪關之后,理想無從安放,人生變得彷徨,由此在網絡吐槽,結果收獲一片罵聲。
原因無他,在于“小仙女”冒犯了全體的低收入群體。
985已經翻身了,進入選調生行列已經是步入成功者行列了,編制已經在板凳下面,體制內的鐵飯碗已經牢牢端在手里了,怎么還吐槽、還嫌棄,還攻擊這個地方是“落后的戈壁灘小縣城”,還說導師不希望她就此成為“野婦”,這不僅僅是赤裸裸的“凡爾賽”,還重擊了那些對此感到遙不可及的低收入者的心理和尊嚴。他們感到了冒犯,感到了反擊的重要性,為此在網絡的各個角落,射出了憤怒的留言子彈。
雖然武大選調生在中高收入群體那里會獲得同情,畢竟理想不能實現,實乃人生痛苦根源之一,正如低收入群體看到有人實現了他們想象中的最高理想,卻棄如敝帚,說些風涼話,由此堅決不能容忍一樣。
如此之廣泛的網絡批評,主要是因為“小仙女”得罪了如此之多的低收入群體。
類似事件還有很多,比如香飄飄愛國營銷事件、“戰馬行動”事件等等,莫不如此。
本文只是通過階層分析的方法,來看一些網絡熱點事件背后爆發的社會心理,來獲得一個新的理解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