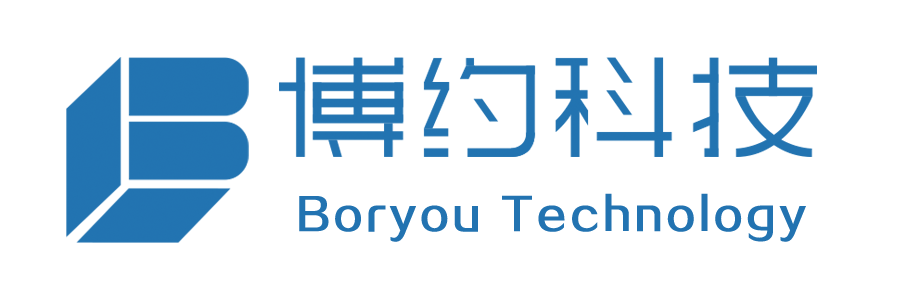當(dāng)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律師的作用和風(fēng)險分析
這段時間,國內(nèi)不少地方發(fā)生了輿情,其中有的事件因為涉及到訴訟,因此律師的身影較為頻繁地出現(xiàn)在事件進程中,出現(xiàn)在微博及其它公共輿論平臺,成為輿論場里的一個值得關(guān)注的現(xiàn)象。
1
清空微博:熱點事件中律師如何制造輿論?
比如在貴州的女企業(yè)家討工程款被捕案中,以及在近期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中,為受害者辯護的律師都在網(wǎng)絡(luò)刷出了較大的存在感,引發(fā)了廣泛的關(guān)注。
人們發(fā)現(xiàn),上面案件的代理律師和有些名記者一樣,都具有曾經(jīng)一戰(zhàn)成名的案例,然后就成為網(wǎng)絡(luò)名人,實現(xiàn)良性循環(huán),越有名越會接到大案,實現(xiàn)了聲望財富的累積。
律師也常常是引爆輿論的高手。一旦就某個案件接受采訪,或者在網(wǎng)絡(luò)爆料,立即就會引發(fā)強烈關(guān)注。近年來,突然清空微博,成為一個常見引爆關(guān)注的手法。網(wǎng)絡(luò)“陰謀論”深得人心,清空微博肯定會吸引網(wǎng)民,主角常常登上熱搜。
比如這位未成年案的代理律師在清空微博后,網(wǎng)絡(luò)一時就出現(xiàn)很多他的信息。人們才關(guān)注到,原來他就是當(dāng)年震驚全國的某個反殺案的辯護律師。這讓人們恍然大悟,很多人開始信心滿滿。因為據(jù)傳,當(dāng)年這個反殺案在他的辯護下出現(xiàn)反轉(zhuǎn),并被認(rèn)為推動了法治的進步。無論事實如何,他擁有這種網(wǎng)絡(luò)光環(huán),不少人寄望于他再次創(chuàng)造歷史。
當(dāng)律師在某個案件中主動刷存在感,并力圖擴大事件影響的時候,常常意味著事件會出現(xiàn)轉(zhuǎn)機,或者意味著某種更大的風(fēng)險。
比如,對于那些弱勢群體遭遇強勢霸凌的案件,律師出面之后大聲疾呼,推動公正審判,很多事件由石沉大海到浮出水面,暴露在陽光下,事件會出現(xiàn)逆轉(zhuǎn);
但是對于那些較為復(fù)雜的案件,律師在輿論上營造較大的影響后,常常會導(dǎo)致一個后果,就是很容易導(dǎo)致輿論審判,煽動民眾情緒怒火,反倒給法律審判帶來壓力。
這是律師的價值和風(fēng)險共存的雙刃劍效應(yīng)。
但是無論如何,預(yù)計律師群體在中國接下來的發(fā)展進程中,參與會越來越頻繁,作用也越來越重要。
2
中國律師群體的四個發(fā)展階段
律師群體的崛起,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常常是其健康發(fā)展和持續(xù)進步的社會顯性指標(biāo)。原因很明顯,他們是法治建設(shè)的推手,而且,他們也常常挑戰(zhàn)公權(quán)力。故步自封的社會,是容不下他們的,也沒有適合他們出生的土壤。
中國年輕的律師群體出現(xiàn)的時間并不算長,但是已經(jīng)給社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重大事件已經(jīng)留下了他們的身影,打上了深深的法治烙印,有的改寫了案件走向和當(dāng)事人的命運,甚至有的注定會載入史冊。
從律師在中國過去數(shù)十年間網(wǎng)絡(luò)輿情中扮演的角色出發(fā),我們基本可以將中國律師群體的變遷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一是群體出現(xiàn)的初級階段。就是在城市化和工業(yè)化之前和初期,他們作為中國法制化(當(dāng)年尚未出現(xiàn)“法治化”的提法)進程中的成果,很多高校的法學(xué)院畢業(yè)生參與了律考,后來改為司法考試,但通過率極低,甚至比注冊會計師都低。今天大熱的國考,當(dāng)年尚未出現(xiàn)。他們?yōu)橹袊姆ㄖ苹峁┝讼鄳?yīng)的法律火種;
二是“死磕律師”群體的出現(xiàn)。“死磕”群體的出現(xiàn),在于城市化、工業(yè)化快速推進的進程中,出現(xiàn)了大量侵害弱勢群體和底層百姓權(quán)益的事件,然后不少律師就挺身而出,和地方政府、地方審理程序進行抗?fàn)帯!八揽摹币婚_始是個被地方人士給出的污名說法,但是后來流傳中成了中性詞,再到最后,被這個群體順勢借用了,反倒成為公正和勇氣的代名詞。這個群體的出現(xiàn),意味著中國律師群體首次大規(guī)模地登上了歷史舞臺,并且產(chǎn)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尤其收獲了弱勢群體的好感。中國百姓首次認(rèn)識到了律師群體的威力,以及他們身上天然帶有的法治氣質(zhì)和挑戰(zhàn)者的勇氣。但是律師也因此給一些地方領(lǐng)導(dǎo)干部、公檢法工作者留下了毀譽參半的印象;
三是律師群體遭遇整頓階段。雖然不少律師打出了名氣,但是不能不說,群體內(nèi)魚龍混雜,有的害群之馬反倒傷害了法治精神,導(dǎo)致全國律協(xié)不斷出面批評和矯正一些不正之風(fēng),強調(diào)和強化行業(yè)自律。一些地方出現(xiàn)抓律師的案件。但正如抓記者一樣,類似案件往往不能獲得百姓支持和同情,如果沒有釋疑解惑的強大輿論,類似案件常常引爆輿情。但是無論如何,“死磕”現(xiàn)象慢慢成為過去時;
四是常態(tài)化發(fā)展階段。社會各方已經(jīng)接受了律師作為社會一個必不可少的法律工作者角色,有案件請律師已經(jīng)成為人們的共識。公檢法不再將其視為異類。這是在“死磕”階段之后慢慢出現(xiàn)的,因為一些死磕律師獲得了成功,通過合法途徑成功將腐敗者、侵害民意者挑落馬下,從而獲得高度評價。這包括上面提到了為反殺案辯護的律師,也包括曾經(jīng)遭遇“黑打”的辯護律師,出獄后江湖名氣日重,成為意見領(lǐng)袖。這個階段他們和體制內(nèi)的法律工作者一道推動了中國法治化的進程。不過,這個進程也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由于和法官等法律工作者處于一個博弈的立場,律師有時也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比如不時會出現(xiàn)法官侮辱性的言行,或者一些律師向法官行賄的案件。
當(dāng)然上述階段的劃分,從律師行業(yè)來看并不精準(zhǔn),僅僅是從輿情的歷史視角來看待的。總體看來,中國的律師群體在中國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雖然有所波折,但是相對比較順利,因為他們這個群體的出現(xiàn)基本順應(yīng)了中國城市化和法治化的潮流,其法治追求和理想實現(xiàn)是和中國政府和社會的發(fā)展方向完全是一致的,各方基本是順潮流而向前發(fā)展。
3
律師群體的角色價值分析
律師群體天生就自帶意見領(lǐng)袖的氣質(zhì),本能上也是期望能夠成為意見領(lǐng)袖的。
這源于律師和記者在很多方面是具有共同的特質(zhì),共享某種內(nèi)在精神:
● 他們都在發(fā)現(xiàn)社會的不完美之處,并力圖在規(guī)則范圍之內(nèi)進行彌補,推動社會更為完善合理;
● 利用合法身份和手段突破某種社會禁錮和權(quán)力框架;
● 更多說話為弱勢群體代言,并進行抗?fàn)帲?/p>
● 為了實現(xiàn)目標(biāo),他們需要向社會呼吁并尋求公眾支持,由此產(chǎn)生社會影響,也因此導(dǎo)致雙刃劍效應(yīng);
● 常常被相關(guān)部門加以防范,因為公權(quán)力永遠(yuǎn)是法律和輿論的監(jiān)督對象;
● 律師成為意見領(lǐng)袖后能夠?qū)崿F(xiàn)良性循環(huán),大律師、大記者常常成為行業(yè)金字塔塔尖的人物;
……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律師的依法代言和記者的輿論監(jiān)督,一旦結(jié)合,往往產(chǎn)生重要影響,并可能導(dǎo)致巨大社會傷害。這在下文要講。
但是律師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特點,這使得他們的貢獻(xiàn)往往能夠超越媒體,在更高的層面推動社會進步。
那就是律師一切工作的準(zhǔn)繩是法律,底線也是法律。這使得他們成為最好的普法人和法律的監(jiān)督者,是法治精神的播火者和布道者。他們作為相關(guān)部門的天然對立者和博弈者,一旦言行舉止失去了法律條文的支撐依據(jù),就直接將自己置于風(fēng)險之地。
他們受到法律、輿論、群眾和公權(quán)力的多重監(jiān)督,他們是法律的囚徒,也因此成為法律的信徒。他們恪守法律不光是職業(yè)特點,更是人身自保武器。
所以我們可以說,律師群體的出現(xiàn),本身是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結(jié)果,是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直接產(chǎn)物,他們形成群體的力量后,又能大大推動社會的進步,畢竟,法治是在封建宗法和人治之后的更為科學(xué)的社會規(guī)范。
當(dāng)然,現(xiàn)實生活是復(fù)雜的,普通的律師收入并不高,很多在為生活而奔波。資源越來越向大律師、資深律師集中,這也使得“搞事”“搞名氣”成為他們的內(nèi)在需求,也使得一些地方為此深感頭痛。也有少數(shù)律師因為作風(fēng)和收費問題搞到聲名狼藉,但是不影響這個群體的正向價值。
4
律師群體的社會風(fēng)險分析
但是,律師群體可能導(dǎo)致的社會風(fēng)險也是非常巨大的。
從職業(yè)看,律師的工作方式,幾乎是以一己之力獨力面對一個異常龐大的系統(tǒng),他的全部合法性和力量的來源,就是法律賦予他的權(quán)利和權(quán)力,以及職業(yè)的正義感。他單槍匹馬,有時候還需要自費取證,一旦失敗,顆粒無收,可能損失慘重。這使得他有強烈的動力贏下案件。
但是他常常槍彈不足,勢單力薄。他所依仗的法律武器,對手也是熟稔于心。法庭之上,你來我往,唇槍舌劍,鹿死誰手,結(jié)果難測。一旦受挫,又常常禍不單行。更何況,很多地方存在基層司法腐敗現(xiàn)象,律師本身有可能淪為案件的犧牲品。
上述種種風(fēng)險,使得律師常常傾向于選擇將案件的成敗,押寶于制造有利的輿論,以及喚起民眾的群體情緒。
也就是在法庭之外,律師將案件通報于媒體或者信息從業(yè)者,然后炒作為社會熱點,引發(fā)大眾討論,從而將法庭內(nèi)的“茶杯里的漣漪”,放大為社會大海的滔天巨浪,通過喚起普通民眾的關(guān)注和憤怒,倒逼法庭做出有利于己,或者順應(yīng)民眾情緒的審判結(jié)果。近年來,甚至出現(xiàn)律師進行“網(wǎng)絡(luò)營銷”,就是熟練使用自媒體和新媒體,在網(wǎng)絡(luò)放大影響,影響案件審理。這種行為,本身反倒是違背法治精神的。
這種法庭外的社會情緒,在網(wǎng)上就是網(wǎng)絡(luò)輿情。這就又回到了網(wǎng)絡(luò)輿情的討論范疇了,那就是線下事件一旦演變?yōu)榫W(wǎng)絡(luò)輿情,平息起來就要頗費功夫,相關(guān)部門常常不得不屈服于這種網(wǎng)絡(luò)輿情,難以嚴(yán)格依法辦案。或者即便頂住壓力依法辦案,還不得不額外考慮:如何安撫網(wǎng)民群體情緒,如何管理網(wǎng)絡(luò)輿情風(fēng)險,以及如何善后,等等。這種綜合運用“情理法”手段才能平息輿情的案件,近年來屢屢發(fā)生,比如在唐山打人案等案件中,表現(xiàn)得格外明顯。作為輿情從業(yè)者,我在看很多通報的時候,常常能夠直觀感受到文字后面和段落之間調(diào)查組各種糾結(jié)、躊躇、不甘以及屈從于大眾的心理活動。
上面提到的這種訴諸法庭外民眾情緒和道德直覺的現(xiàn)象,就是輿論審判。輿論審判常常不是依據(jù)法律,而是依據(jù)道德直覺、人心向背,以及民眾的當(dāng)下群體情緒。這種情緒的背后,是數(shù)千年來民間快意恩仇的俠義情結(jié),以及對于青天大老爺“驚堂木一拍,人頭落地”的心理爽感模式。但是問題是,這樣操作下,法律反倒蒙冤,真相可能被綁架。
輿論審判和司法審判的沖突,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解的矛盾,并非中國所獨有。但是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以及行政力量較為強大的情況下,律師常常要面對多重壓力,訴諸輿論然后獲得輿論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一點。這種輿論一旦爆發(fā),往往演化為輿論審判。
輿論審判一旦出現(xiàn),就會導(dǎo)致網(wǎng)民對于審判結(jié)果的強烈期待,而這種期待潛藏著強烈的沖突性,因為一旦現(xiàn)實結(jié)果和自己輿論審判的結(jié)果不一致,或者未達(dá)心理預(yù)期,群體怒火就會點燃,剩下的一地雞毛和遍地狼藉,都需要審判部門和相關(guān)部門來應(yīng)對、來善后。
5
此次未成年罪案中代理律師的巨大動力
法理情,和情理法,在中國的現(xiàn)實社會和網(wǎng)絡(luò)社會邊界模糊的交錯空間里,常常產(chǎn)生異常復(fù)雜的復(fù)合反應(yīng)。
法,是法律層面,指的制度建設(shè);理,是理性層面,指的輿論、民心;情,是情感道德層面,指的常常波動的個體或者群體情緒。尤其法和情,在網(wǎng)絡(luò)輿情里常常出現(xiàn)拉扯現(xiàn)象,吵架的結(jié)果,常常是“法”忍氣吞聲,“情”揚眉吐氣,“理”在中間,左右為難。
所以我們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中國,越講理,越容易吵架,越吵越遠(yuǎn),社會撕裂現(xiàn)象由此產(chǎn)生。這源于情緒的支配力量越來越大了。“后真相”時代的來臨,摧毀了傳統(tǒng)社會的理性基礎(chǔ)。
“情”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產(chǎn)生的影響越來越強,網(wǎng)民群體的情緒化流量,常常對的現(xiàn)實產(chǎn)生摧毀性的壓力,這讓執(zhí)法司法部門深感敬畏。
律師在博取輿論優(yōu)勢方面,有巨大內(nèi)在需求,也常常比體制內(nèi)部門更為舒展,資源更多。這源于體制內(nèi)受到嚴(yán)格的制度約束,并且視輿論為某種風(fēng)險,這實際是固守城池,城池之外廣闊天地,都讓給律師,利于后者放開手腳。但是這種手腳也是需要“戴著鐐銬跳舞的”。比如,上面提到的律師清空微博,根據(jù)網(wǎng)絡(luò)信息,在于律師在制造輿論、證據(jù)獲取、新媒體傳播中,已經(jīng)涉嫌違規(guī),于是只能進行刪除,但是刪除和清空本身,又引發(fā)輿情。
即便相關(guān)部門提醒律師不得挑撥網(wǎng)民情緒,防范輿論審判的現(xiàn)象,但是這種努力是很難奏效的。因為在今天的網(wǎng)絡(luò)透明時代,任何一個重要事件,都會引發(fā)網(wǎng)民的大規(guī)模的圍觀,并且在各種碎片化信息滿天飛、真相拼盤尚未成型的時候,已經(jīng)自發(fā)形成輿論審判。即便律師保持獨立,但是網(wǎng)絡(luò)民意和網(wǎng)絡(luò)審判結(jié)果已經(jīng)成形,律師要做的不過是順應(yīng)、或者引導(dǎo)、或者扭轉(zhuǎn)的問題。所以,事實上網(wǎng)絡(luò)輿情對于律師是天然有利的。
就以此前多起大案來說,比如某地那個著名的反殺案,都是處于大規(guī)模網(wǎng)民的密切關(guān)注之下進行司法審判的,為此不得不做出各種輿情預(yù)案和應(yīng)急預(yù)案,防范可能的風(fēng)險。
那些獲得成功的律師,包括上面提到的有名律師,在當(dāng)年的優(yōu)勢在于,案件已經(jīng)演化為網(wǎng)絡(luò)輿情,司法審判如履薄冰,律師只要順應(yīng)這種網(wǎng)民訴求,就能起到四兩撥千斤之效,畢竟網(wǎng)民已經(jīng)掌握了事態(tài)進展的方向盤,自己順應(yīng)潮流,就能轉(zhuǎn)動整個齒輪,勝訴也就是水到渠成。
這意味著,很多今天的大律師,常常是輿情的獲益者,以及某種程度上輿論的操控者。
因此,當(dāng)某個著名律師介入某個重要案件的時候,可能本身就意味著風(fēng)險。因為他不再是一個人,除了他背后的律師群體資源,還有輿情和網(wǎng)民情緒的加持。無論是逆境還是順境,他都可以醞釀引爆或者利用輿情。
就以當(dāng)下人們關(guān)注的這個未成年犯罪案來說,代理律師有強烈的動力,再次創(chuàng)造歷史。或者延續(xù)此前的網(wǎng)絡(luò)傳奇。
而且這種條件相當(dāng)成熟,因為無數(shù)網(wǎng)民希望嚴(yán)重的未成年犯罪者要受到嚴(yán)懲,乃至死刑。律師只要順應(yīng)網(wǎng)民呼聲,再進行適當(dāng)?shù)娜后w情緒挑撥,就會形成巨大壓力。即便失敗,也會成為悲劇英雄;一旦成功,將載入史冊。這種動力和誘惑,無疑是巨大的。
這種個人英雄主義在律師群體那里,是一種被鼓勵的個體勇氣,和進行建功立業(yè)的巨大動力。但是對于法律和主管部門來說,意味著巨大的風(fēng)險和壓力。
6
如何降低“律師+輿情”的風(fēng)險?
下面的文字,聽起來會有點“反思怪”的感覺,但是這種反思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就是,律師之所以能夠號令輿情,網(wǎng)民之所以在網(wǎng)絡(luò)圍觀案件,并且引發(fā)群體情緒,背后常常是對于當(dāng)下法治環(huán)境的各種不信任。比如,司法腐敗現(xiàn)象、地方領(lǐng)導(dǎo)干部干涉司法現(xiàn)象、法官不平等對待律師現(xiàn)象等,都增加了輿情爆發(fā)和輿論審判的風(fēng)險。
我們從輿情爆發(fā)的根源來看,本來就是網(wǎng)民對于地方政府和公權(quán)力的不信任乃至抵觸,從而引發(fā)網(wǎng)絡(luò)圍觀。
從律師的所作所為看,他們試圖影響輿論的做法固然有獲取優(yōu)勢的因素,但是不能不說,他們這個群體對于中國法律環(huán)境和司法底細(xì),是最為熟悉的群體之一。為了抗衡各種壓力,讓陽光罩住自己,他們也又可能尋求輿論的支持。因為這也是一個社會原理,那就是任何事件一旦放到輿論之下、推進到公共輿論之中,事件和自己,反倒會安全了。因為網(wǎng)民的圍觀,構(gòu)成了強大的監(jiān)督,任何公權(quán)力和特權(quán),在這里都會遭遇拷問。
因此,對于相關(guān)部門來說,如果想盡可能降低律師操弄輿論以及網(wǎng)絡(luò)輿情爆發(fā)風(fēng)險,那么就應(yīng)該盡力創(chuàng)造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法律氛圍,真正推進法治化進程。
而一個公正合理的社會環(huán)境,本身就是降低輿情爆發(fā)可能性的條件。輿情不那么容易引爆了,律師就失去了可以依賴的外部環(huán)境,反倒能夠促進法治精神的回歸。
如果把律師比喻成海中翻騰的蛟龍,那么輿情和網(wǎng)民情緒就是增加他能量的巨浪。一旦大海風(fēng)平浪靜,兩者反倒都消停了。
所以說,很多事情看起來復(fù)雜異常,但是一旦找到了問題的根源,脈絡(luò)反倒變得一目了然了。